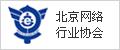和静钧 西南政法大学副教授
肇始于去年春的叙利亚内乱,并没有出现突尼斯式的倏变,而是呈现渐变又反复的事态发展特征:先是单纯的分散和局部反政府示威,之后上升为复杂的分散和局部的反政府骚乱和教派冲突,然后再升级到首都以外地区的武装冲突。现在,胡拉惨案之后,随着安南“六点建议”基本挫败,叙国内出现多点同时爆发武装对抗,一些地区被反政府武装所控制,可以说,叙国内冲突已经质变或处于质变的边缘,即陷入内战。
大体而言,从中东北非这轮动荡的共性出发,目前危机解决至少出现了三种既有模式:利比亚模式、也门模式、埃及模式。在探寻叙利亚问题解决之路中,不可能避开对这些模式的试探性启发。
先看“利比亚模式”。利比亚反对派在班加西建立有“全国过渡委员会”,叙反对派也建立了一个“全国委员会”;利比亚反对派武装从一盘散沙,到最后训练有素,经历了半年多时间;叙利亚反对派的“自由军”也呈现这样的态势,从弱到强,装备与兵力不断在提升。目前,叙利亚与利比亚模式不同的一个明显地方是:利反对派有一处获得国际社会保护的国内领土班加西作为基地,而叙利亚现在尚未能稳稳在国内某一地方上立足,“全国委员会”的总部还寄居于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而“自由军”则藏身于土叙边境的土耳其一侧,在那里受训。一旦“自由军”在边境地区一大片领土上获得控制权,土耳其或国际社会有可能在此地区上设定“禁飞区”。
“利比亚模式”无法移植到叙利亚身上的原因很明显。首先,国际社会加诸卡扎菲头上的“制裁与禁令”,难以在巴沙尔身上奏效。卡扎菲倒台数年前与西方改善关系,利比亚统治者及家属的大量转移到欧美的资产,可以成为欧美为战争埋单的有效资产,而叙利亚长期与欧美失和,在欧美几乎无投资,冻结与扣押巴沙尔及家属在欧美的资产之余地几乎没有。还有一个重要障碍是,安理会很难通过一个针对卡扎菲那样的“授权采取一切措施”的决议。
叙利亚最后会不会通过“利比亚模式”解决,取决于叙“全国委员会”在国际上被承认的程度,也取决于“自由军”军事行动的进展。刚刚当选为“全国委员会主席”的库尔德人阿卜杜勒·巴斯特·西达,呼吁巴沙尔军队中的军官“叛逃”或“投诚”,让人们想起卡扎菲最后阶段众叛亲离的结局。
第二个模式是“也门模式”,也就是通过第三方介入调解之下的权力退出模式。也门与叙利亚均为世俗政权国家,然两国教派矛盾的深度与广度并不相同,萨利赫没有教派包袱,而巴沙尔有。也门问题上,支持萨利赫的海合会主导了萨利赫的退出谈判,叙利亚问题上,则不存在这样的主导力量,从而会让巴沙尔看到既有权力不受到损失的机会,使其不会认真对待国际社会对其“退出”的呼吁。
15个月的冲突,导致2万人死亡,20多万人沦为难民,百万人需要人道主义援助。冲突越恶化,“也门模式”越不可能成为解决叙利亚问题的可资模式,巴沙尔即便退出,其责任被豁免的机会也已经不存在。
第三个模式则是“埃及模式”。埃及模式的本质就是亲原政权的军人发动一场不流血的“政变”,并由军方来主持政权的过渡。长期以来,埃及军方受美援助,中层军官多数在美培训,在政权合法性的状态取向上必然受到美方的军队中立的影响。而叙利亚军方几乎与欧美无交往,作为俄罗斯地区盟友,装备的主要是俄式武器。从军事体制上看,巴沙尔直接掌握死忠于自己的精锐部队,军事政变以实现政权更迭的可能性也基本不存在客观条件,假如真有一场政变,那将是一场血流成河的政变。
这样一来,我们通过上述分析,大体可以掌握叙利亚的形势发展趋势:在近一段时间之内,并无直接和现实的外部军事干预的可能性存在,内战中的叙利亚反对派,将保持力量增强的态势,其目标将是在叙利亚境内开辟“牢固的根据地”。内战的本质是冲突双边都拥有了宣布对方非法的能力,是政权正当性的重新洗牌,双方相互搏杀之后的胜方,将以原始权力取得者(战胜者)的身份重整河山。一旦叙利亚真正陷入内战,之前基于国内冲突的角度来制订其对外政策的国家,将面临调整和重构对叙利亚关系的挑战。这15个月的冲突表明,巴沙尔翻转形势的可能性已经越来越渺茫。





























 京公网安备 11010202007241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20200724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