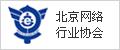很少人知道,农历三月三是苍蝇诞,也就是苍蝇的生日。这一天,粤西农民会做一些番薯点心,用小棍子插着,为苍蝇庆生。苍蝇即使再可恶,它的存在也是应该被尊重的。既然与人类为邻,朝夕相见,为它们庆生,也是很有人情味的做法。传统农民保留的这个“奇怪”的习俗,背后隐含着多少生存的智慧。由此联想到,十年前春天,震惊世界的“非典”诞生了;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把今天作为它的生日,每年为它庆生呢?
瑞典病理学家FolkeHenschen曾说:“人类的历史即其疾病的历史。”
事实上,历史中几次大的传染病深远地影响甚至改变了西方文明史。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进一步解释这一关系:“在世界历史上,任何一次传染病的流行,都是人类文明进程所带来的;反过来,每一次大规模的传染病又对人类文明本身产生极其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这是一个总的概念。”
2003年突如其来的SARS,让国内学者从不同领域作了反思,同样的,科学人文学者也对科学技术以及人与自然、人与细菌、人与环境的关系作了反思。
时隔10年,我们回顾当时,再次听听身在其中的科学人文学者的思考。
自然的报复
SARS带给人们最大的提示莫过于科学技术的局限。
原本人们认为细菌病毒在抗生素时代完全是有克星的,结果SARS来无影去无踪,没有克星,不知道其发病机理,也没有有效办法去应对。
在控制SARS疫情的发展上,最先进的技术没有派上用场,真正让SARS得到控制的是传统的隔离方法。
科学技术高度发展,以致有一部分人就把科学当成万能的,把技术当成万能的,北京大学教授刘华杰在谈到SARS时说:“随着科技的发展、生产力的提高,人类有一种幻觉,以为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是无限的,即使碰壁了,人们还会认为‘我们终将超越障碍’,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实现。”
“现代技术是一个网,让我们想从中反叛都无可凭借。”北京大学教授吴国盛在谈到现代技术的本质时说,“现代很多技术哲学家一再呼吁技术时代的危险,但危险并不在于环境灾难、核电站泄漏、飞机失事,这些都是表面现象,真正的危险在于我们对于危险本身不知不觉,我们不知道有危险。”
已故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当时曾撰文说要反思科学:“抗击SARS、防治传染病是用科学知识来救人,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科学一时还跟不上。人类要反思,科学的进步到底该落到哪里,是毁灭人类还是造福人类,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这关系到文明的前途。”
对于SARS这场灾难,人们不禁要问:是谁造就了超级病毒,它的来源是什么?它为什么会出现这么恶毒的效果?思考结论还是因为人类自己。
北京大学医学部教授王一方说原因就有两个:一是对环境的侵入,二是抗生素的大量使用。
尽管不清楚SARS病毒来自哪里,但是随着人类活动范围的不断扩张而导致原始自然环境的日益缩减,生物物种的减少,人类势必侵犯了许多病毒的藏身领地,迫使它们显露出来,从而侵袭人类。
这再次促使人们反思人类与动物、微生物之间的生态学关系,想到人与自然的关系,想到“敬畏自然”。
美国思想史家纳什撰写的《大自然的权利》,清楚地讲述了许多思想家是如何一步一步扩大伦理主体范围的,虽然纳什本人持保留意见,但他的思想史著作启发人们尊重外物,敬畏自然。
刘华杰认为,站在“非人类中心论”的立场上看问题,人类不会失去什么,相反能够超越自己,更好地倾听自然的箫声,理解大地的意图,使我们的行为与自然之间更加和谐。而过分强调“人类中心论”,人类不会因此而伟大起来,相反人类的狂妄要受到自然的“报复”。
“20世纪的人类科学提示我们,对于不可预测或者尚未预测的东西,人还是要谦虚一些为好。这也是敬畏自然的一条重要理由。与未来、与自然打赌,谦逊一点,就相当于多给自己留了一条后路。”刘华杰说。





























 京公网安备 11010202007241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202007241号